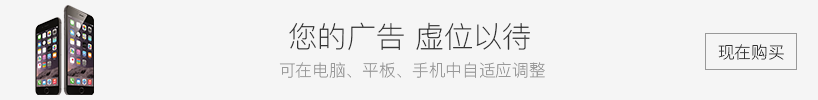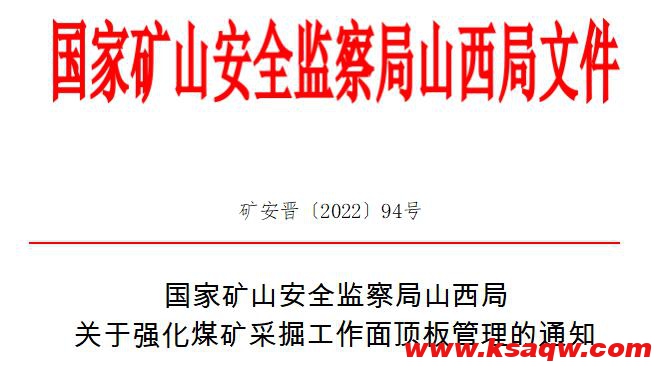高兴兰
我的父亲是一名矿工。一顶安全帽,头戴矿灯头,一条矿灯线连接背上的矿灯瓶,腰间系一条皮带,套着矿灯瓶背在背上,满脸像涂抹着锅底的黑色,一身粗蓝大布的劳保服,脚穿一双水靴鞋,走过36个春夏秋冬,从未改变过。这就是我的父亲井下作业时特有的全副武装。
父亲生于1926年,因家境贫穷,童年是在泪水和汗水中泡大。听母亲讲,父亲九岁时就去给一家私人煤厂当童工。那时的煤洞矮小,更无从谈安全设施。井内无光线,挖煤靠火把或松油灯照明,摸着路拖煤。父亲拖着半筐煤,跟在大人的后面,肩上被绳索裂出一道道干茧。衣服磨烂了,就光着身子,从煤洞爬进爬出,要不是两只眼球的转动看得出是活人,还以为是一节木炭。所以,当地老百姓把拖煤的人叫“拖炭手”。
岁月承载着父亲的童年和“拖炭手”的头衔,由私人小煤厂走到资本家开的大煤厂,从事井下作业。
那是1942年,资本家、袍哥大爷汪XX获取了大蚕溪(大塘溪)、捏颈子煤井的开采权后,新建“民生私人煤厂”,开发方斗山的煤炭资源。大蚕溪和捏颈子,位于重庆市石柱县万朝乡境内方斗山,海拔在615——1042米之间。父亲最初在大蚕溪给资本家开厂,长年累月一直从事井下作业,也逐渐摸索出一套井下全面维修的经验,成为厂里工人们的师傅。
解放后,国家接管了方斗山“民生私营煤厂”,建立“公营丰都煤矿”。不久,“公营丰都煤矿”移交忠县人民政府经营,更名为“公营忠县煤矿。”1956年,煤矿隶属四川省,后又下放给万县专区管辖。无论煤矿历史如何更迭,父亲始终没有走出煤矿,成为解放后第一批正式国营煤矿工人,维修技术骨干,参与煤矿开厂打坝事项,改善矿井设施设备条件。父亲进厂得早,熟悉井下生产作业,便常告诫他的徒弟:“井下维修分巷道维修、掘进维修、采区维修,是一项技术性强,危险性大的工种。”维修一般是夜间作业,将掘进、采煤后危险的地方,留给维修工去处理。父亲带着徒弟们用木料装箱、打顶子、裂缝修补或局部维修等,只要哪里有需要就奔向哪里,天天与木头打交道。
1957年,捏颈子井凿穿煤层后,大蚕溪煤厂改名为一井,捏颈子井为二井,父亲从一井调往二井,仍从事井下全面维修。二井离我们家约20里路,小时我去过,至今我还记起那条小道,从方斗山脚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梯路,上到山腰便是矿工的厂区。从山腰到山脚有一个长滑槽,煤从滑槽滑到山脚,由煤车运往忠县东溪口上船,运往祖国需要的地方。煤质好,在阳光的照耀下,成放射性的光柱体,闪烁耀眼。
井下作业是黑暗、艰苦、危险的代名词。其作业分采煤、掘进、机电、运输、通风、排水等工种,一环扣一环,每一项都出不得差错。可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1959年5月31日,捏颈子(二井)北大巷发生瓦斯爆炸事故。事故发生后,父亲参与对死伤人员的抢救,从矿渣里刨出一具具遇难的工友。事故造成死亡42人,重伤1人,轻伤1人。这天父亲没有按惯例回家,母亲在家有些着急,不停地安慰自己,不会有事的。第二天,父亲回家了,母亲见父亲不高兴,问是怎么回事?父亲长长叹了口气说:“二井出事了。上班的时候都是好好的,出来时却成一具具尸体。”说着眼圈都湿了。从那以后,父亲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:“进去后要活着出来才算人。”
矿井不仅随时有生命危险发生,而且干活很苦很累。看着父亲满是茧子的手,粗糙得像松树皮一样,干裂成一道道口子,指关节常用蓝线系着。我那时很不理解,以为那样好看,便学着父亲的样,也用蓝线系在自己手指上。后来才明白,那是父亲井下维修,没有手套,常年握手锤,震裂的一道道口子。一道口子还未愈合,另一道口子又出现。尤其是到了冬天,父亲的手特别粗糙,皮肤易脆,手指关节的蓝线有增无减。春去冬来,父亲走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,终于有了转机。
1964年,同属方斗山脉的三井凿穿煤层后,父亲又调往三井作维修技术骨干。因离家近,父亲白天可多休息会。
无论是一井还是二井、三井,一年复一年,屈指算来,父亲从解放前到解放后,从事井下维修36年,负过一次伤,留下伤痕伴终生;父亲带出的徒弟也不少,哪里有危险的地方哪里就有父亲的身影。徒弟们深有感触地说:“只要有师傅在我们身边,我们就感到踏实。”父亲过硬的技术,工作吃苦耐劳,任劳任怨,得到矿领导和矿工的好评,曾多次在职工大会上作先进事迹报告,获煤矿优秀矿工,先进工作者称号。父亲带出的徒弟,有的还走上矿领导岗位。
父亲在煤矿是技术骨干、好师傅、好矿工;在家里是好父亲、好靠山。可天有不测风云,父亲在一次意外事故离我们而去,走时还带着满身的泥土和对儿女们的不舍,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父走如山倒,一走近40年。逝者长已矣,存者永思念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阴阳相隔,父亲一去杳无音信,一切都断线了,唯有那层层叠叠的记忆和思念,却永不断线,时常把我带回童年,想起父亲远去的背影,内心深感愧疚,直到今天,常伤心落泪。
岁月悠悠,往事历历。那是我国正面临的三年特殊时期,那时我还不到七岁,家里缺粮断炊是难免的。我们三姊妹就像巢中待哺的鸟,盼着父母的归来。
一天,父亲带回三两大米,那是父亲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口粮,叫我到地里弄些菜回来煮粥。说完后,父亲去帮母亲干活了。我在家煮了满满一鼎罐(炊具)菜粥,我们全吃光了。过了一会,父亲回来了,问:“煮的饭还有不?”我一下懵了,结结巴巴地说:“我们全吃完了。”父亲不用再问了,饿着肚子,挑着一担空粪桶,朝上班的方向走去。因那时农村没有化肥,自留地的农作物全靠农家肥浇灌。父亲上夜班,每晚9点进,凌晨4点钟出,休息几个小时后,上午就从厂矿挑一担人大粪走回家,下午又去上班。
多少年过去了,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,想起父亲远去的背影,我感受到了父亲的艰辛,心里不由自责,泪水夺眶而出。那时太不懂事了,怎么就没想到父母还没吃饭呢?当我懂事后,父亲又走了,在我的灵魂深处时时不能原谅自己,更不能用一片童心来为自己开脱。
好不容易度过困难时期,我属学龄儿童,也渴望上学读书。可在那个年代,农村女孩上学读书是少之又少。尤其是生长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夹皮沟,女孩读书更是不容易。人们的思想守旧,认为女孩长大后是别人家的,培养也是帮别人家培养。在我们生产队,比我年长或是同龄的女孩都没上学读书。我父亲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头,不顾世俗的偏见,坚持送我上学。
那时的小学校是在一个村小,学校设在一座寺庙里,只有一间教室,一位老师,而且还是复式班。四年级的学生有七八人,坐在教室的前排,在老师的眼皮之下;一年级的学生坐在后面,老师讲完大同学的课后再给小同学上课,我就这样糊里糊涂读了一年。
一年后,父亲就把我转学到忠县煤矿子弟学校读书,因父亲是煤矿工人,沾了点光。我是农村孩子,学校“独一苗”,其他同学都是工人或是干部子女,父亲把当月省吃俭用的钱给我买皮鞋、缝新衣;母亲把家里省下的玉米、大米,留着给我带到学校蒸作午饭吃,享受特殊伙食。父母所做的一切,只为我在学校不受人欺负。后来,在父母的带动下,我们生产队的女孩都上学读书了,小学、大学、研究生都有。长大后,山里孩子往外走,县城、重庆、成都、上海,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,但还是走不出父母的视线和牵挂。
我工作后,在离家二十多里地的一所小学教书,父母还是担心我的冷暖。那时交通不便,每到冬天,父亲徒步给我送棉被、棉衣,还将木材断成一小节一小节的,划成一块一块,便于我开小灶好堆放和使用。放假后我回到家,父母总留下好吃的让给我吃。父母心里满满的都是爱,装着的是我们六姊妹,唯独没有他们自己。我成家后,有了孩子,才深深地体会到,父母的牵挂是长期的,都饱含着无限的心血,留下那一份尽在不言中的疼爱。
父爱像一座山,背负着最大的压力,托起沉甸甸的希望,却累弯了自己的腰板;父爱是一种岁月,张开双臂,敞开胸怀,成为我们安全的港湾。想起父亲的饱经风霜,累了一生,苦了一生,为儿女付出一生的爱,却没享一天福,我心里就酸酸的,泪眼婆娑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当我一天天变老的时候,对父亲的思念日渐加深。时间留不住,能留住的是岁月的记忆。即使天人永隔,依旧是我深切的思念。无限的关怀,无限的牵挂,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父亲的节俭、勤劳、慈善的一生是一本我永远读不完的书。
作者简介:
高兴兰(笔名:兰草),女 ,土家族,重庆市人,毕业于西南大学文学院,重庆市作协会员,曾从事中学语文教学、纪检监察工作、林业工作和编修地方志工作。先后有散文、论文、人物通讯、评论等多篇文章在《中国地方志》《中国监察》《中国民族报》《重庆日报》《重庆文艺》《重庆晚报》《重庆晨报》《贵州民族报》《巴人》《运河》《检察文学》等报刊发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