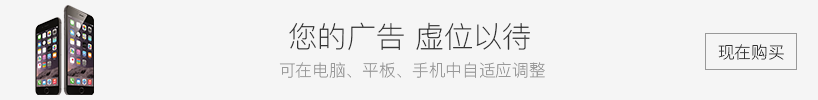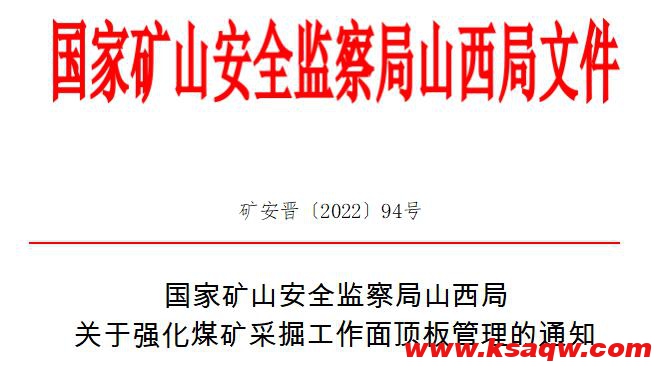矿山中秋月儿圆
作者:闫桂花
往些年,矿山的灯与火是从近处亮到远处,远到一座又一座的山坡,远到一条又一条的沟里,处处都是烟火气息。家里灶膛的火从不熄灭,灶膛的笼屉里给下井人留着热腾腾的饭菜,随时回来可以吃。矿山的孩子们满街乱跑,磕一下碰一下,拍拍打打就跑远了。那些靠下井人养活的家属们,从简单的衣食住行里,一样延伸出理想、希望及未来,这一切让生活变得色彩斑斓。
最具色彩斑斓的该是过年过节了。年的热闹自不必说,而真正讲究的节,就是中秋节。因为只有中秋节,才可以吃到各类瓜果,吃到新鲜的粮食。中秋节快到时,家家户户都精打细算着。白面是从平时供应的口粮里攒下来的,攒十几斤白面不容易。白糖或是红糖都是凭票供应,也得攒一攒才够用。攒下来的这些东西送到打月饼的铺子里,家家就能端回还冒着热气的月饼。离我家不远处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月饼匠,他曾是在村镇做月饼点心的小徒,后来来矿上当了工人。每年一到八月初一,他就利用闲余时间,开始试灶给人们打月饼。人们也就陆陆续续,开始排队打月饼了。我母亲每年打月饼的时候要打一个“月儿圆”。什么是“月儿圆”呢?就是比普通的月饼要大上好几倍,里面还包着好吃的五仁馅,这个“月儿圆”是非常有讲究的,必须是八月十五晚上供完月亮才能吃,而且家里有多少人切多少块,还要给祖先留出供奉的份儿。
中秋节这天,母亲早早就张罗晚饭。全家十几口人聚在一起不容易,母亲极尽心思,变化着饭菜的品种与花样。天刚蒙蒙黑,母亲便在小院里摆上小方桌,桌子上放着用西瓜刻出的花篮,红艳艳的很是喜庆。那时候水果不及如今的丰富,但也有海棠果、小冰果、苹果和梨,最抢眼的当然是桌子中央的那个“月儿圆”了。灯光一照,“月儿圆”泛着惹人食欲的光泽。当然,还要摆上一盘普通的月饼。过节么,谁馋了就先吃点普通月饼,只有月亮品尝过“月儿圆”,母亲才会切开分给大家吃。再有一个亮点就是,母亲要把家里祖传的铜盆拿出来,在盆里倒上半盆水,等月亮升起时,盆里就有一个月亮了,那个装在盆里的月亮勾起我们无穷的想象,嫦娥、吴刚、玉兔都有,我们指着水里的月亮说:“看见了,看见了。”节日的欢声笑语在空气中凝聚成幸福的种子,这种子种在心田里一生一世都开着花,结着果。也有的年份碰上“天狗吃月亮”,母亲就会敲着铜盆,我们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敲着铜盆,慢慢地就把月亮“救”出来了。
中秋节这天,母亲反复告诫家人,这一天要好好地讲话,谁也不要说过了头的话,更不许吵架,她还安顿父亲不能责备我们。母亲说,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,过年过节是攒福气的最好时候。母亲问我:“你给妈说说,福气是什么?”我半天答不上来。母亲就说:“福气就是家里人相互感恩,福气就是家里人好言好语,福气就是家里人你疼我爱。”父亲在一旁有些不耐烦了,他说:“你看你那点儿远见,还教育孩子呢,天天就是家里人家里人的,邻里朋友亲戚就不处了?”母亲从不与父亲争执,只是笑笑,就忙别的事情去了。其实,有的人家在过年聚集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,家庭成员之间种种的矛盾总是在节日里爆发出来。而正是母亲的这种性格,我们的家庭才是一派祥和的景象。
中秋节这天,两个哥哥是要陪父亲小酌一杯的。那时候喝酒是三钱的小杯杯,慢慢倒,慢慢品。
与如今的人们喝酒不一样,那时,喝酒人很惜福。酒是节日的重头戏,父亲往桌子中间一坐,两个哥哥左右陪着,大哥给父亲斟满酒时,二哥也已经给大哥斟满酒,再给自己倒上,他们三人干上一小杯,便开始找话题聊着。更多的时候是夸夸父亲,父亲被夸得沾沾自喜,难免会多饮几杯。母亲平时总是告诉我们,父亲和兄长是养家的功臣,这话是说给我和姐姐及侄儿们,也是说给两个嫂嫂。两个嫂嫂也不争高低,在她们看来,母亲就是她们的榜样。母亲吃素食,两个嫂嫂进了门后,她们也跟着母亲一起吃素食。听邻里们说,娶过的媳妇像婆婆,家才能长久延续下去。这话也有那么点儿意思。如今,大哥和大嫂都七十多岁了,二哥和二嫂也近七十岁了,他们都是一生相依相伴的模范夫妻。他们也都和当年的父母一样,儿孙绕膝,福泽绵绵。
父亲与兄长们喝酒中间,月亮已经升到半空中了,月光洒在小小的院落里,落在每个人的脸上,每个人的脸上都透着喜悦,心情也是格外地舒展。也就是在这时候,母亲开始切“月儿圆”了。侄儿从母亲手里接过一块“月儿圆”,快快跑到父亲的身边,“爷爷,爷爷”地喊着。父亲忙不迭地接在手里咬一口,还不忘让他的孙子在“月儿圆”上也咬一口。家里每一个人的手里都有一块“月儿圆”,美美地吃着,谈天说地,好不热闹。那种聊天就是从地上往天上聊的天,喜悦无边,欢乐无边。
父亲母亲过世后,当年一起吃“月儿圆”的场景也只能在梦里遇见了。如今的矿山人都搬出山坡与沟壑了,他们住进了棚改新区,住进了做梦都想住的楼房。他们感受着矿山的变迁与发展,也享受着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成果,在这个过程中,好像是当年小家庭的那个“月儿圆”变成了大大的“月儿圆”,每家每户都分到了他们的“月儿圆”,家家户户的幸福也汇聚成了新时代的发展之歌,真正实现了矿山中秋“月儿圆”。